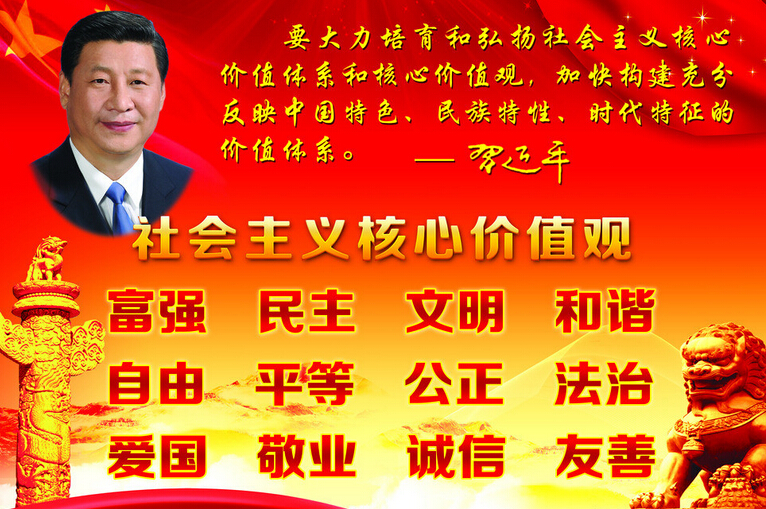- UID
- 79380
- 帖子
- 4585
- 积分
- 33001
- 阅读权限
- 80
- 注册时间
- 2008-2-23
- 最后登录
- 2015-5-26
- 在线时间
- 7841 小时
|
炡椨出面挖皇陵【转】
古今中外,炡椨出面挖皇陵的多了,今天我们看看新中国是怎么做的。在央视《人物》栏目里,亲耳听到八十多岁的赵其昌等讲述他们挖掘定陵的往事。
1955年秋,六位当时赫赫有名的人物郭沫若、沈雁冰、吴晗、邓拓、范文澜和时任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张苏联名向国务院写报告,要求炡椨组织挖掘明十三陵中最大的长陵(朱棣之陵)。总理周恩来大笔一挥,批了四个字:“同意发掘。”
就这么简单?就这么简单。就这么容易?就这么容易。
当时身为考古研究所副所长(所长是郑振铎先生)并主管业务的夏鼐是反对挖掘的,但他没有能力阻止,还得承担起发掘的指导工作。具体干事的是他的学生赵其昌,赵担任挖掘工作队队长的职务。在长陵勘察了三天后,赵其昌说,长陵规模太大了,能否找一个较小的陵墓先行试掘,积累了经验再动长陵?这点吴晗倒与夏鼐意见完全一致,可以多挖一座,为什么要少挖一座呢?我想,明史专家吴晗先生是这样思考问题的。吴同时提议,可以把目标放在定陵,因为定陵的主人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,在位48年,史料可能丰富些;另外,定陵营建年代较晚,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,将来修复起来也较容易。
在仔细辨析定陵外罗城城墙的残迹后,赵其昌又跟夏鼐反复商议,定陵的修成距离万历下葬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,城墙上应该有地宫入口的明显标志,以便皇帝驾崩后能迅速找到地下出口……按照这个思路,他们果然发现了金刚墙外的夯土地沟,又发现了那块“距金刚墙十三丈”的标记石,然后顺利找到地下甬道,直抵金刚墙门。在风凉过几天后,赵其昌也没戴什么防毒面具,腰上拴着根绳,拿着镐头、手电筒进到金刚墙内。翻进金刚墙,就算是进到地下陵寝内了,拴绳子进去,是怕墓内有传说中的暗器机关,特别是翻板之类。
方法也太小儿科了,也太黑看先人了。先人也太放心这些后代儿孙们了。
据记载,整个定陵的开掘自1956年5月破土动工,到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结束,历时两年零两个月,以总计用工两万余、耗资四十余万元。
定陵地宫内出土了大量色彩明丽的织锦布匹,每匹上面都有织匠的名姓,布匹之都用纸条夹隔着。因为没有相应的技术人员,又缺乏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准备,出土几天后退色、变色,许多东西都化为灰烬,根本无从保持完整。还有些袍服的处理,从外国看来一点资料,再把英文翻译成中文,再请化工专家现场配比试验,做成“塑料”,再用这种“塑料”加入软化剂涂在半腐的衣服上,时间稍久,衣服颜色变深,软化剂蒸发,质料变硬,硬作一块,遂无法展开,这类工作后来只能停止。
当时有人建议,丝织匹料可以像古画一样进行托裱,背后衬用韧性大的纸张,以便卷舒;有人建议,糨糊内加入防腐剂,以便长久保存。文学家沈从文也是专门研究古代服饰的大家,他也过来凑热闹,想看看匹料,回去做点研究。将裱品展开,用放大镜一件件仔细观察,随后迷惑不解地问:“怎么有的装裱成品显露的是织品反面?”“研究织品的结构不是要看反面吗?”一位工作人员急中生智说。一句话激怒了沈从文,但他还是面带微笑地说:“研究织品结构,要看反面,更要看正面。如果为显示反面结构,留下一厘米、两厘米,最多五厘米也足够了。整匹反面,我看是装裱的错误。”他的直言不讳,使站在旁边的负责人十分尴尬。沈从文不愿再看下去了,走出接待室,对同来的助手说:“囊括了中华纺织技艺精华的明代织锦遗产,如此轻率地对待,还做这样不负责任的解释,不是出于无知,就是有意欺骗!”我看沈从文就有当总理的水平。
定陵丝织品损坏的消息传出后,郑振铎、夏鼐等大吃一惊。正焦虑不安、痛心疾首呢,外地又传来消息,说有的省份正在组织人力,跃跃欲试,要向帝王陵墓进军。汉陵、唐陵、清陵,都响起了开掘号子……郑、夏心急如焚,立即上书国务院,请求对这种极不正常的发掘之风予以制止。幸好周恩来批准了郑振铎他们的建议。只是吴晗还是心有不甘,自定陵“试掘”后,他还一直想着怎么继续借着总理的批示去“正式”开挖长陵。有一次见到周便问,“我们是否再发掘长陵?”总理说,“需要多少钱?”“大约要四十万。”总理没有说话,向停放在不远处的轿车走去。吴晗着急地追问:“总理,您看这长陵发掘的事?”周恩来在沉思片刻后说道:“我对死人不感兴趣。”
我看这话就看不明白,他是疼事呢还是疼钱呢?
“文革”开始后,造反派试图摧毁明楼,却因明楼用料坚固异常,未能得逞。他们在竖匾的“定陵”二字上刷上油漆后,又闯入了地宫,最后砸碎棺椁,又将万历帝后的三具古尸全都焚毁了。《人物》栏目里,一位参加过定陵挖掘工作老队员说,“红卫兵来后,将帝后的遗骨弄到(定陵博物馆前)广场上烧,当时我在场,烧的时候我没过去看。”那天是1966年8月24日,这个日子注定要成为中国考古史上最悲怆的日子。应该感谢中国生产力的落后,红卫兵的不学无术,创造一个旧世界不会,连砸烂一个旧世界也不能。
有一部不知道拍摄年代的彩色纪录片,记录了定陵部分挖掘过程,明眼人能看出来,许多镜头应该都是后来补拍的,比如用铁丝做环套住顶门石,然后推开地下宫门(从切换的几个角度就可以看出漏洞来。八十年代以前,中国自己拍摄的几乎所有纪录片,政治的或者其它的,都有大量的作秀成份,比如解放军进上海、攻克南京总统府、北平和平解放等等,跟苏联人学习么)……片子最后,有文革音质的女播音员说,“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,相信不久的将来,这片过去的禁地,一定会成为新中国历史最大的地下文物展览馆。”
八十多岁的赵其昌对着镜头缓缓地说,“我总有一种历史负罪感。但(掘陵)这个我没能力做到,那么谁应该有这个能力做到呢?……必定,这是经由我手里挖掘的。”老头晚年将家搬迁到十三陵脚下不远处一个不起眼的农家小院子里,他没有说明原因。在这里,他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陵寝”,养花,弄草,刻石,其中刻了一方石就叫“掘皇陵人”。
定陵挖掘鼓噪的最厉害的是专门研究《明史》的专家吴晗。吴晗的结局很悲惨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?还有另一个挖墓大主使,郭沫若先生,他不知道亲临挖掘现场几回了,从定陵文物中感悟出多少哲理,研究出多大的成果,好像都没了下文。他好像还很关心武则天的乾陵,也是没有下文。我只是知道,郭氏现在早就被网民批驳的体无完肤、斯文扫地。 |
|